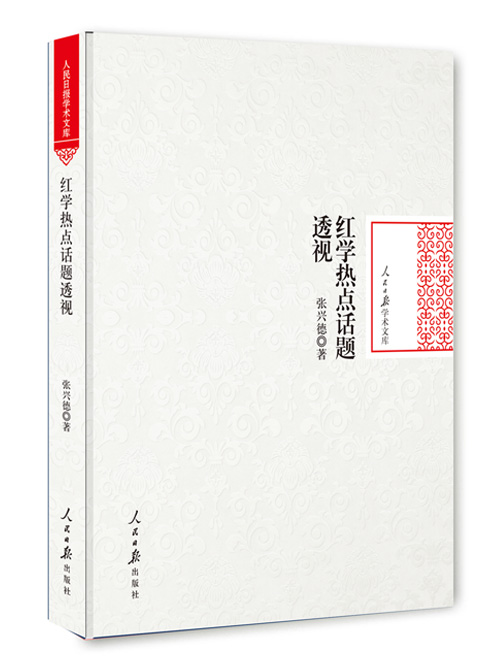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发表的红学论文选集。作者对有些长期流行的红学观点和理论提出了质疑和商榷;对目前红学中许多重大而敏感的、热点的话题进行了辨析和讨论。
作者对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红楼梦》解读的“泛娱乐化、非文学作品化、非学术化和神秘化”的现象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概括,对其存在的理论和社会根源进行了全面、科学分析。
作者简介
张兴德 1941年生,鹤岗市人。1960年参军,1987年转业到大连市中山区宣传部工作。中国红学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散文学会会员。先后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40余家报纸杂志和大学学报发表数百篇学术理论、诗歌散文等文章。有十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等书报转载(摘转)。著有红学专著《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
(一)
红学的迷失与红楼文化的危机
面对《红楼梦》,该有怎样的“使命感”?
(二)
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
——论《红楼梦》中的忧患意识思想
红楼梦中无哲学吗?
对宝玉的“封建社会叛逆说”质疑
“为闺阁昭传”说质疑
——兼谈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目的
是“真事隐去”,还是“真实(思想)隐去”?
全面辩证地看《红楼梦》中的“虚无思想”
绕开脂批看可卿
是“辨是非”好,还是“辨是谁”好?
——关于元春判词一处重要异文的辨析与商榷
也释“老天拔地”
(三)
关于全面、辩证、科学地看脂批问题
——回应俞平伯先生在晚年红学研究自省之一
对《红楼梦》传承的“返祖现象”的反思
——回应俞平伯先生在晚年红学研究自省之二厚重的历史回应
——回应俞平伯先生在晚年红学研究自省之三
读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
——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学研究反思之四
当代红学新索隐、探佚派的负面影响与谬误
腰斩《红楼梦》:错误的研究方法、可悲的文化现象
——坚持正确地评价标准,科学认识、充分肯定后四十回的
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红学研究中的泛娱乐化、非文学化、非学术化问题
再谈关于正确认识“程高本”的几个问题
——2014年在铁岭高鹗与《红楼梦》的学术会上的发言稿
(四)
从学术层面看1954年的“批俞评红”
——重读何其芳等旧文想到的
对“批俞评红”的再认识
——纪念“批俞评红”60周年
关于客观、全面、辩证地认识“批俞评红”的几个问题
——兼答刘绪源先生
附录:俞平伯的红学观转变
——兼谈对1954年“批俞评红”的再认识
(五)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在《红楼梦》艺术构思中的重要作用
王熙凤两次治丧不同结果的哲理启示
从小说视角看“风月宝鉴”的哲理意蕴
《好了歌解》与《司马季主论卜》
细品红楼(两则)
读《红楼梦》为什么不宜提倡“浅阅读”?
——答一位青年朋友问
(六)
红楼画卷的赏析与解读
——读胡文彬先生的《〈红楼梦〉与北京》
“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的红学研究
——读胡文彬先生的近作《感悟红楼》兼论目前红学的一种倾向
甘当学友不为师
——读《红楼两地书》
文学评论家应有的操守
——读《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想到的
(七)
附录1:站在哲学高度解读《红楼梦》
附录2:一部力图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学术著作
——张兴德的《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
后记
红学的迷失与红楼文化的危机
孙伟科先生在《文艺报》(2012年2月29日第3版)著文,提出了“热闹的红楼文化”“包含着深刻的危机”,“举步维艰”的红学,应该“成为文化创造力之学”。这在当前无疑是一个极为有意义的话题,但同时也是一个须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的问题。
首先,如何全面、辩证、正确的评析当前红学和“红楼文化”的形势或状况,应该有个共识的标准和视角——这就是应立足于是否有利于正确宣传、传承、普及文化“国宝”《红楼梦》。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红楼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国宝”,我们这一代人,不仅应该从《红楼梦》吸取其丰富的文化乳汁,以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同时,更要正确地宣传、普及、传承《红楼梦》,这是我们的光荣义务和责任。
红楼文化的产生和出现几乎是同《红楼梦》的流传同步的。最早的红楼诗词、红楼绘画、红楼曲艺等,其实是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用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解读和表达,它在《红楼梦》流传史上起着普及、宣传《红楼梦》的积极作用。
红楼文化的变异和危机是近几年的事情,它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许多是商业的逐利的巨手在操控,例如所谓红楼餐饮之类。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红楼文化的发展、变异和危机,同红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红学通过不同途经在影响红楼文化。当前红楼文化包含的危机与红学的迷失有极大的关系。例如,令一些人着迷、甚至趋之若鹜的“揭秘红楼”和“探轶”《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故事”的兴起和走红,这已经不单单是红楼文化了,它已经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对它关心的热度和广度已经超过了小说《红楼梦》本身。而作为一种“红楼揭秘”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和形成,其源是受红学研究中的所谓“探轶学”的影响。而再追溯这“探轶学”的产生,则是源于胡适当年的否定后四十回。本来,程伟元、高鹗当年经过多方努力,使当年“无定本”“无完璧”的《红楼梦》,得以以120回本(就是后来被人们统称为“程本”的《红楼梦》)的面目流传。胡适否定后四十回的这一做法,被他的继承者们加以放大并推向极致,在无确凿可靠证据的情况下,硬说程伟元是一介书商,程伟元出于商业的逐利,编造了《红楼梦》后四十回成书的假话,高鹗则是受皇帝的旨意,窜改了前八十回,就这样,后四十回被彻底否定了,程本的前八十回也被基本否定。而把来历不清、面目不明的脂砚斋的批语作为研究后四十回的权威根据,于是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所谓“探轶学”。这本来是红学研究的一派观点。在红学界从来没有统一过。从学术研究角度说,就是再研究一千年也无可厚非。但是,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出现了一部以否定后四十回为特征的八七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继之,强势媒体又大力讲述、宣传“揭秘红楼梦”“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故事”之类,这样,连中学生都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伪续”。于是,原本属于红学界内部的“一家言”,便成了一种社会的文化现象。其影响所及,不仅直接干扰了人们阅读《红楼梦》文本,它的直接和间接危害是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乐此不疲地跟着一些人去探寻这些“真故事”,而对《红楼梦》本身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含蓄蕴藉的艺术却少有(无暇)问津了。而且,由此还使人们产生一些猎奇心理,于是,各种“雷人”的学说纷起(例如有人甚至要“拯救红楼梦”)。致使《红楼梦》研究出现了泛娱乐化、非文学作品化、非学术化和神秘化的怪现象,把本来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附加了种种“特异功能”。至于孙先生说的一些人在“没有一些可靠的文献根据”的情况下,自立学说,其实也源于当年否定后四十回的胡适及其后一些追随者们的影响。他们在否定后四十回,否定程伟元、高鹗的自序时,也是“没有一些可靠的文献根据”的。
历史是最好的证人,历史又是一面镜子。《红楼梦》流传二百余年来,泽被广远,它的“乳汁”,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诚如孙先生所列举的鲁迅、茅盾、巴金等人。而这“乳汁”,并不是现代红学家们刻意论证的什么“红楼后四十回的真故事”;也不是一些红学家乐此不疲地考证的曹雪芹的祖宗的祖宗;也不是来历不明、面目不清的脂砚斋究竟是谁和他的批语;也不是那个“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什么真、假本《红楼梦》的问题;更不是《红楼梦》背后映射的清宫秘史的“秦学”之类;这些一代文化大家,所接受和吸取的不过都是那个120回本《红楼梦》一书本身所体现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含蓄蕴藉的艺术及其高度结合的魅力。这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一切研究《红楼梦》的人们不应忽视的。
其实,哀叹红学“举步维艰”,这正是对红学研究的一种迷失。《红楼梦》作为一部文艺作品,其欣赏自然可以是多视角的、全方位的,正所谓“一百个读者心里可以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是,红学史告诉我们:《红楼梦》引起的多起纷争,确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包括正确解读)《红楼梦》本身所体现的思想和艺术的问题。俞平伯先生晚年在他还很清醒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外界影响的情况下,认真地总结了他的红学研究,很负责任地自省说: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又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对俞平伯先生的这个认真的反思,红学界至今处于失语状态。还有,从胡适创立新红学到20个世纪50年代的批评俞平伯和七十年代的全民“评红”,这些重要事件,虽然从总体上已经有了结论。但是,遗留下来的许多理论问题尚须要重新研究和认识;有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须要去做;有许许多多的混乱认识须要厘清;“文革”的“左”的影响,还在或明或暗地在影响我们对全书的思想内容以至于对人物思想形象的解读,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在红楼梦研究中也有或明和暗的反映,等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置上述这些大量的“选题”不顾,却哀叹“举步维艰”,这不能不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迷失。
(原载于《文艺报》2012年4月25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