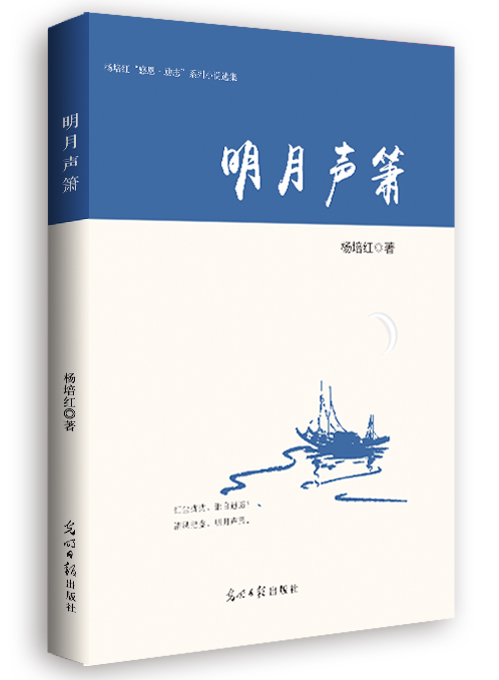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本书系杨培红“感恩·励志”系列小说选集。故事发生的时间,发生在20世纪末至当下,正值社会从封闭保守到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地域特色鲜明的川东北深丘大地。四川盆地东北部曾有一个迷失的国度——充国,她经历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西充位于盆地中部偏北,是嘉陵江与涪江的脊骨地带,这样一个小县,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言谈举止,特别是方音俚语,不说跟周边大城市重庆、成都、南充、渠县、广元、巴中等相去甚远,就连跟直线距离不超过30公里的顺庆、南都、阆中、仪陇、盐亭也有很大出入。我们甚至怀疑,这儿也许就是那个从巴国分离出的神秘小国——充国的祖籍地。作者蛰伏在生活的底层,平时城市和乡村,借笔下人物的命运,让我们透视社会现实,感受人物的辛酸苦辣。故事一个又一个,虽是一些红尘俗事、风土变迁,却也悲欢离合、富有哲理,且不事雕琢,娓娓吟来,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折射出村镇的叠影和时代的嬗变。
作者简介
杨培红 四川西充人。发表各类文章200余篇,其中有“感恩·励志”系列长篇小说《潮湿的翅膀》《且行且吟》《老何所依》《明月声箫》等。2006年主编学生优秀文集《青春的花朵》;2008年出版文集《红烛燃情》;2010年出版文集《星月共辉》(2012年再版);2016年出版农村养老题材长篇小说《老何所依》(签约深圳天铧影视);2019年出版小说集《明月声箫》。《重庆晚报》、《南充日报》、凤凰网、西充电视台等20多家媒体专题报道其事迹。
太阳滚坡的时候,庄稼地里一片静寂。
桃花河边的这一坝苞谷苗,生长得蓬蓬勃勃。暑气还没退,又没丁点儿风,烘热得很。苞谷秆儿哨兵般纹丝不动,叶片儿静静地低垂着。桃花河两岸虔诚而庄严。
毛毛背着书包,悠悠然出现在河边。书包挺漂亮,由几块红白相间的皮革镶嵌而成。里面塞着一本小人画《阿A爬山记》。要是有人碰见,毛毛会昂着头挺起胸理直气壮地回答:“到姥姥家去呢。”姥姥住在桃花河流去的地方,没有人会怀疑的。
毛毛在河边转悠着,黑亮的眸子鹰隼般地扫描着株株挺拔的苞谷苗。苞谷丰满得很,挂着长长的胡须,沉甸甸的,翘得像牛角。毛毛咕咕咕地咽了一通口水。
这一坝苞谷,是胡子爷爷的责任田。胡子爷爷有一个争气的儿子,在城里种子公司工作,给胡子爷爷捎回一小袋种子,说是什么良种,外国进口的。如今全村人的苞谷还只是破土的苗苗,胡子爷爷的苞谷就已经挂上了红红的胡须。
“哥,我要吃苞谷,苞谷……”
这是妹妹的声音,微弱得很,像来自遥远的地方,又好像来自苞谷地那深邃的密匝匝处。毛毛心虚了,没有了先前的自信和神气。
要是妈妈在就好了!毛毛眼里差点滚出泪水,伤心地想。
早晨,东方天际刚吐白,妈妈就忙忙碌碌地收拾起了行李,吩咐毛毛说,爸爸长年在外打工,妈妈要到爸爸那儿去,说不准明天还是后天才能回来。当时毛毛正在困被窝,听说妈妈要去县城了,就一骨碌翻身嚷着要跟去,肥肥的屁股把那薄薄的被子撅得老高。妈妈神色仓皇,还是很耐心地说进城不是去玩,爸爸在建筑工地干活,出了工伤事故,毛毛乖乖,在家看好屋,看好妹妹。毛毛是个听话的孩子,隆起的被盖又瘪了下去。妈妈不放心,又交代了一遍,还说如果遇上麻烦,就找胡子爷爷。毛毛摸摸身边的妹妹红红的脸蛋,像鸡啄米似的点了无数个头。妈妈回头看了三眼,待被子彻底瘪下去了,才无奈地扭回头,匆匆离开了。
毛毛虚汗出了一身,脑壳倒清醒了不少。胡子爷爷真好玩,六十多岁,身板硬朗,田间地里样样行,天南地北门门知。毛毛他们最爱缠在胡子爷爷身边,听他大嗓门地神吹。毛毛印象最深的是下面这个故事:桃花河的下游是黄河。黄河是条泥沙河,黄河是条天上河。黄河一旦缺口失水呀,那可不得了。当初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打不过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夹着尾巴逃跑时,用飞机坦克大炮炸了花园口堤坝,结果黄河水像脱缰的野马,排山倒海,雷霆万钧。房屋、树木、庄稼、山峦、牲畜,一切东西灰飞烟灭,大地变成汪洋大海。有不少的人被黄河水冲到渤海,冲到了太平洋,随着汹涌的波涛,又冲到太平洋那边的美国,冲到了美国的旧金山上。结果《纽约时报》上刊登了黄种人尸骨漫山遍野的消息,丢了中国人的脸,丢了老祖宗的脸。该剐的国民党,是真正的垮民党,让小日本的铁蹄踏入中国,烧杀抢掠。还是共产党好,带领人民赶走了强盗,打倒了欺压劳苦大众的黑恶势力,亿万中国人获得了解放,挺起了腰杆,当家做了主人。人民像个大家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毛毛他们听得目瞪口呆,父母们拖着声音吆喝“回家吃饭”也不理。然而最有趣的,还是胡子爷爷那稀稀疏疏的胡子。
胡子爷爷走路的时候,胡子迎风而动,飘飘洒洒,很有一种小人书上说的仙风道骨的味儿。在他讲故事的时候,胡子一翘一翘的,好像在助兴;而在他激动的时候,胡子又会索索地颤抖,让人忍不住想笑。
有一次听故事,毛毛想入非非开了小差,手痒痒得慌,就悄悄地伸手过去,想摸胡子。
“啪!”的一声,大手打在小手上,清脆却不疼痛。
胡子爷爷一巴掌拍下,横眉怒骂:“狗崽子,小心打断你的狗爪爪。”
于是大家就“咯咯咯咯”地大笑起来。听人说胡子爷爷脾气犟得很,发起怒来像一头公牛;可是,毛毛从没有看见胡子爷爷公牛过。
毛毛把眼光移向远处。桃花河上浮起一层薄薄的带状水汽,朦胧迷人,远处房顶上长出了炊烟袅袅的尾巴。
河边有一块斜斜的绿茵茵的草地,是毛毛他们的乐园。今天中午,毛毛经不住伙伴们轰轰烈烈的诱惑,带妹妹来到河边。河水清亮,金色的太阳从头顶干干净净地直射下来,河面闪烁着光怪陆离的波影,就连绿茵茵的草地也染上了一层耀眼的色彩。几条小鱼调皮地蹿出水面,划了几个漂亮的小圈儿。一只精致的小鸟,在那婆娑的柳树上轻松而醉心地欢叫。一声“跳哟”,毛毛他们便扑噗噗地扎进水里,巴掌大的鱼儿就被抛上岸,落在了草坪上,落在了妹妹的眼皮下。妹妹乐得直跺小脚,小手张牙舞爪地乱抓。忽然“扑通”一声,妹妹跟着一条鲤鱼,活蹦乱跳地栽进了河里……
“叽叽叽……”有昆虫在河边凑热闹了。
远山在浅亮的苍穹下,勾勒出几条淡淡的墨色。
毛毛翻开《阿A爬山记》,里面写了阿A这样一个故事:“阿A爬山了。
阿A来到山脚,发现路旁有一棵非常高大的苹果树,红艳艳的苹果压弯了大树的腰,一直垂到地上。几个熟透了的苹果落在地上,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阿A脑子里打起了小九九,心想:何不趁现在背几个苹果到山顶,到时好好庆祝一下,还可解渴呢。
于是,阿A就在苹果堆里拣来拣去,拣了好几个大大的红苹果。接着,他又开始爬坡了,可是,越爬越累,越爬越慢……
结果,阿A口冒白沫,直喘粗气,累得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了……”毛毛有点瞧不起阿A。他想,阿A真笨,不动脑子,可以先吃苹果啊,有了力气,不就可以继续爬山么?
“苞谷,苞谷……”妹妹两片薄薄的嘴唇颤了颤,梦魇般地吐出了一丝声息。
妹妹浑身精湿,昏沉沉地睡了一个下午。毛毛闯祸了,摸摸妹妹的额头,热热的烫手。毛毛记起妈妈的话,用冷毛巾给妹妹搭在额头。远远流去的桃花河水,信息流不到姥姥那儿。毛毛又去找胡子爷爷,可是胡子爷爷在哪儿呢?到处都没有他的身影。
“苞谷,苞谷……”毛毛明白了,妹妹想吃苞谷。
毛毛有点瞧不起自己了,阿A爬山笨,自己也聪明不到哪儿去,妹妹生病了,自己咋就没有办法了呢?毛毛想啊想,忽然记起了绿豆稀饭,只要自己一生病,就打心眼里渴求绿豆稀饭。妈妈再累再忙,也要把香喷喷的绿豆稀饭端到面前。这东西比穿白大褂阿姨手中的针药还灵,毛毛每次吃了,病儿就会好上一大半。
毛毛终于记起了桃花河边的这一坝苞谷地。中午摸鱼时,妹妹不是眼皮直直地盯着苞谷瞅了半天么?
妈妈是不会回来了,胡子爷爷呢,毛毛也没找到。
“苞谷,苞谷……”妹妹终于醒了,嘴里要的仍是苞谷。
毛毛犹豫了,但最终还是背上书包上路了。
老师,原谅我吧!妈妈,原谅我吧!胡子爷爷,对不起了。毛毛不再犹豫,倏地窜进庄稼地,寂静的河边有了簌簌簌簌的响声。
“妈的,天未黑定就出来了!明天老子上街花两毛钱,回来让你吃个四仰八叉。”
河岸,传来了苍老却如洪钟的声音。
糟了,是胡子爷爷!毛毛不禁毛骨悚然,背上冷飕飕地透过一股寒气,额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脚步声响了,越来越密,越来越近,稳稳地踩在毛毛稚弱的心尖。毛毛被吓破了胆,尿湿了裤子,怀里的苞谷扑簌簌直往下掉。
胡子爷爷不再认为是耗子、夜猫子什么了,更不会冤枉两毛钱再去街头买耗子药了,他几大步窜过来,像拧起一只小鸡似的把毛毛拎了出来。
“是你?”胡子爷爷瞪着一双浑浊的老眼,牙齿咯咯咯地响。眼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馋猫们痒痒的喉咙里早伸出了手,没想到最先想一饱口福的竟是村里的乖乖儿毛毛。
毛毛噤若寒蝉,眼睛直勾着脚尖。先前的充分准备和自信倾刻间荡然无存。
胡子爷爷的胡子开始翘了,既而颤颤栗栗。此刻,煞是好玩的胡子一点也激不起毛毛的兴趣。不,毛毛此刻纯粹是讨厌胡子了,毛毛此刻知道什么叫胡子爷爷公牛了。
五块鲜嫩嫩的苞谷零散地躺在毛毛脚边,压在爬山的“阿A”身上。胡子爷爷弓起腰,捡起一块苞谷,拨开顶部的青皮,指甲一掐,乳白色的嫩浆便渗流下来。晚风轻拂,甜香诱人。毛毛口内生津,要不是小嘴轻闭,准会发出挺响的咕隆声。
“走,找你妈去!”胡子爷爷一攀毛毛的臂膀,毛毛站立不稳,趔趄着重重地摔在地上。
胡子爷爷一把拉将起来,说:“走呀!”
毛毛没有喊,没有叫。他好委屈,泪珠儿嗒吧嗒吧地直往下掉,落在那胖胖的苞谷上,继而又溅开了一朵朵小小的水花。
“妈妈……妈妈不在家……”毛毛好伤心。一提到妈妈,毛毛的泪水就汹涌而出。他想起了老师教的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妈妈不在家?”胡子爷爷呼呼呼地火气终于熄了。
毛毛抽抽噎噎地结巴了半天,什么都说了,结果什么都没说清。
胡子爷爷似乎明白了,一边用书包装着地上鲜嫩嫩的苞谷,一边吼着:“还不快走!”说完又转身在地里掰了两块大苞谷。
胡子爷爷变得年轻了,拉着毛毛的手,大步流星地朝毛毛家走去。那长长的胡须随着河边晚风轻轻拂动,很有点仙风道骨的味儿。
暮色越来越浓了,村子里已经有人上了灯,稀稀疏疏、朦朦胧胧而又闪闪烁烁,多么宁静、祥谧、甜美的山村的夜哟!桃红
看来,六月桃红的时节,不再似桃红想象般的美丽。
最近这几个月,桃红一直心事重重。
桃红和柳青在深圳认识。他们一个在服装厂上班,一个在园林干活。元旦休假,两个单位组织员工郊游,俩人不期而遇。萍水相逢后的几句交谈使他们得知对方是老乡——四川西充的。于是,柳青在同事那儿要了这位长发及腰女孩的电话,并给对方拨了过去。当时,对方没搭理。桃红在公司不说是一只凤凰,也算半只孔雀,根本没接这个身材细高个的电话,连手机响了都没觑一眼。
柳青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红着脸走了。
其实,桃红对这个“眼镜”还是有好感的,觉得他除了身体稍显单薄外,眉目清朗,皮肤白皙,有点书生样儿;要不,为啥在对方走后不多久,她还是把号码存进了自己的手机?
那以后,对柳青一两次没话找话的简短问候,桃红总是爱理不理,两人似乎没有什么交集。
春节很快就到了,各地打工的人儿像候鸟一样各自飞回了老巢。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倒也相安无事。
春节转瞬即逝,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少有的人口大迁徙又在中国大地上演了。桃红有些失落,这个春节,父母煞费苦心地托人给她介绍了一门亲事,相面后,她却毫不犹豫拒绝了。再过几天,桃红也要像其他候鸟一样准备南归,面对大包小包的东西,无意间想到了柳青。这一两个月,那死鬼咋就没电话呢?于是翻出号码,小心翼翼地拨了过去。
还好,电话那头有了动静,是柳青的声音,有点激动:“我还说你踢了我呢?”
桃红的小心脏有点失律,自欺欺人说:“咋会呢?在等你电话呢!”
对方好像没听见,说:“我已经辞工了,没打算再出去。”
“你啷个的哦?换地方了?跳槽了?……”桃红大惊,热情骤减,脑海里发出一连串惊问,跟着又冒出一句,“你要结婚了么?”
“结啥婚啰,八字没得一撇。”柳青在电话那头,不紧不慢地说,“我不想到哪儿去了,只想留在老家,经营这一弯一百多棵桃树。”
这个春节,柳青没闲着,核实了先前打听到的消息,趁柳家咀村委会组织坝坝宴的机会,把那荒草丛生的几十亩桃林租了过来,平地、除草、剪枝、撒药、施肥……这桃林原本有一个主子,外地的,因到处非法集资,欠下一屁股债,丢下这个烂摊子,逃之夭夭了。
桃红有点落寞,自言自语地说:“守着大城市不待,神经病……”忽觉失态,立即给自我圆场,打趣想,一头脑壳进水了的猪么?
“你来看看啊,柳家咀这地方可好了,桃树壮着呢……”柳青肯定没听见,只管再三再四地邀请,“西充又不大,交通也方便,走西古公路,个把小时就到了……我在路边等着。”
时间还早,反正无事可做,充国香桃园也算出名,只当是观光旅游吧。桃红这么一想,心里宽慰了许多,就一个人悄悄赶来了。
桃林紧邻西古公路,柳青早已等在路边,待桃红一下车,就迎了上去。
两个年轻人在桃林里转悠起来。
柳家咀位于山腰,似白头山脸侧嘟出的一截长长的嘴巴。这儿地势开阔,从下到上,共四层,下松上紧,层层错落,如同天然垒砌而成的不规则金字塔。几百棵桃树整齐有序地霸占着这一方领地。
柳青说:“你来早了。花开时节,这儿好看得很哦。”
桃红嘟着嘴说:“我是来早了……”
柳青没有察觉,问:“花开的时候,桃红的时候,你都可以回来,到时回来看看不?”
桃红脑袋一扭,一头秀发飞扬起来,说:“花开的时候,我不得回来;桃红的时候,我也不得回来;桃熟的时候,可以考虑哦……”
柳青有点懵,憨憨地笑着说:“到时包你满意哦,说话算数不?”
“到时……到时,全部由你做东哦!”桃红笑了,脸蛋笑成了一朵桃花。
“那就是我家房屋,走,去坐坐,喝口水!”
顺着柳青手指的方向,桃红的眼睛射向不远处的一桩两层楼的房屋,白墙青瓦,鲜亮醒目,墙壁上还依稀可见有几幅乡村民俗壁画:有以桃树桃花为背景、嫁接了杜牧笔下的牧童,有齐白石手中的龙虾、郑板桥身边的青竹、李可染放养的水牛……更远处,浅丘起伏有序,沟壑纵横似画。桃红仿佛看见了一阵春风吹过,桃花竞相绽放,醉霞绯云,曼妙斑斓……
桃红没有去喝口水,也没去坐坐,不到一个小时,两人便各自东西。
春汛汹汹,桃华灼灼,成千上万亩的桃花阵,强烈地诱惑着七县八地的游客。卖水果的,卖烧烤的,卖小吃的,卖土特产的……在乡村公路旁摆起了长龙。
“我这儿的桃花最绚丽的哦,是最佳取景点,拍照的游客可多了……”桃红身在深圳,请不到假,只能想像着电话里柳青喜悦洋溢的显摆,翻看着微信里传递过来的一张张照片。
照片里,柳家咀桃林花开成阵,红红白白,如烟似霞,和青山碧水搭配成了一幅优雅别致的色彩画。
照片里,男男女女眉开眼笑,在地边,在地央,在树下,在树上,三五成群,有的自拍,有的婚拍,有的群照……
照片里,来来往往的游客像过节似的络绎不绝。桃树下的泥土,有的簇新平整,有的板结如铁。很明显,这“铁”是游客千脚万步踩炼的成果。桃红有些心疼了,心想,这真是头猪了,一头没有思想的猪,要是我来经营,非收费不可。若要进园,不多,一人十元……桃红掰起手指,桃花节按一个月算……每天进园按五六十人算……
照片里,树下的泥土上,开挖的沟渠里,红的、白的、粉的花瓣,密密匝匝,有的还未曾落地,飞舞在半空。难道是风雨春归二月天的“桃花雨”?不对,游客们不是穿着新崭崭的休闲鞋么?不是没打雨伞么?透过照片深处,桃红定睛发现,有几个顽童正双手抱着桃枝,似乎在用力地摇晃……旁边,大人们手握相机,专注地定格拍摄。
原来“桃花雨”是这样产生的。桃红依稀看到了桃树花枝乱颤,落红飞泪,心里掠过一丝悲凉。猪头,脑袋进水了的猪头……看来,我不得回去自寻烦恼了,一个正常人,怎么能跟猪头混杂一起呢?
五月桃红,桃红没有回去。
六月桃熟,桃红不想回去。
“你回来看看就知道啦。几万斤香桃,不看后悔一阵子,不尝后悔一辈子哦……”大家都说不清是多少次邀请和被邀请了。
桃红到底是有主见的桃红,她想看看究竟。在六月桃红的季节,她硬是撒谎,千里迢迢请假回来了。
柳家咀的桃子,因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降水丰富,无霜期长而形似蟠桃,白里透红,味道清香,口感脆酥。大道边,停放着一批又一批前来拖货的小车、货车,牌号来自成都、重庆、西安、巴中、广元、南充、遂宁、广安……
柳青笑意盈盈,汗水涔涔,忙得不可开交;手机时不时响,原来是外地客户咨询,指名要他家的桃子……
桃红终于看不过,手脚麻利地做起了下手,帮着客户摘桃、装箱……
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山村恢复了宁静。
桃红搞不清柳青为啥有这么多客户,远的、近的、知名的,还有不知名的?
这有个啥嘛?桃花节期间,到我这片桃林来观光的,我分文不取,还做向导。游客们要了我的电话,都说这片地的位置好,桃子肯定错不了……再说,他们踩踏了我的地,自身还过意不去呢?柳青自信满满地说。
“娃儿们摇花,你就不担心少挂果?”桃红疑虑重重。
这有个啥?他们大都是留守儿童,平时少有大人陪同,难得有这样一份快乐。难道你不觉得他们天真烂漫吗?其实,果子是不得少挂的,当时桃花已经开始谢了,摇摇树枝,不会影响挂果的;即使有点影响,那耐打的花朵结出的果子也是大个的。
柳青不以为然,侃侃而谈,忽地,话锋一转,拉着桃红的手,像商量更像是命令:“你就不出去了,和我一起经营这片桃林,如何?譬如,搞个大型农家乐,食宿游乐一条龙;譬如,闲时设计几十套时装,在花开时节,给游客们备着,应时摄影拍照……”
桃红猝不及防,一下慌了神,心房打鼓噗噗直跳,幸亏有夜幕遮掩,才不见人面桃红。
小溪边,一阵风吹来,桃香弥散在山村原野的角角落落……前嫌
钥匙钻进锁子眼里。
一拧,没动。
再使劲一拧,发出脆裂的一声。啊!断了。
晦气!他觉得真他妈的晦气。他想今天下午的会议要迟到了,于是就眼巴巴地望着她每次回家要走的那条胡同。
胡同里出现了不少人,并且来到了他家门口。以前他是这些人中平等的一员,半个月前时来运转,提升为厂里一个小小的科长。
大家很随便一句“怎么呢”的询问,就弄清了缘由,于是都驻足不前且显得很热心地为科长出谋划策。
有人提出合理利用时间,趁科长等她的当儿应弄出锁眼中露出的那段星光亮色的断匙。大家都显得很主动。
用指甲抠。
用镊子夹。
用铁丝钩。
甚至,运用了物理学的震动原理。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枉费心机。
有人就装模作样地摇摇头准备离去,这时候小张一步三晃地悠来。
他不负众望,回到二楼拿来了一瓶晶亮的液体,在铁丝的一端沾上少许后插进锁眼里,转眼就牵出了那截令大家咬牙切齿的断匙。
大家就很感激小张,也很感激小张那瓶晶亮的液体。有人断言那是一瓶“法国夜巴黎亿能胶精”。
“捣娘的,死了!”科长眼里冒火。
大家蓦地愣过神来。
就在科长愤愤然的骂声顺着胡同传播的时候,胡同口出现了科长的她秀丽的身影。
她的出现反而使科长暴跳如雷失去了当科长半个月来所修炼的涵养,她来到科长跟前麻利地把自己颀长的身体上上下下一阵仔细按摩,然后孩子般恍然大悟地眨动妩媚的双眼,说:
“忘了,我记起钥匙挂在车床上了。”
下午重要的会议无论如何要迟到了,科长想。这时候赶回厂里去取钥匙几乎不成事实,因为骑车来回至少也得花二十分钟。于是科长不断地张大嘴恨不得把她吃了而又不知如何下口,于是抑制不住手痒想去刮她两个耳刮子。
科长这一念头刚一闪现时小张又帮他解了燃眉之急。小张借来一只凳子,放在门前,一脚踹上去,疼得凳子扭曲着身体“吱吱”直叫,然后扬起手一掌击在门楣上方的小窗上。
大家眼睛里出现一片惊异的神色: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脑袋,这么多思想,咋就没想到有这么一处活动机关?
反正门楣上方的活页窗一开缝,问题就彻底解决了。科长泥鳅般窜进屋,顾不上午饭,抓起公文包和有关资料就开会去了。科长的她兔子般蹦进房间时没有忘记对小张报以灿烂的一笑。她却永远也不会知道小张还免了她两个耳刮子的皮肉之苦。
会议一结束,科长春风满面地赶回小屋。
此刻,她正勇敢地站在方凳上一上一下地挥舞着钉锤。他不动声色而莫名其妙地看着她把一颗、二颗、三颗……一共八颗雪亮的钉子牢牢地钉在门楣的活页窗上。
他把双手插进长长的头发里寻问啷个的时候,她却神秘地莞尔一笑,要他先去看看别个家再说。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来到邻居家,发现他们的活页窗都已不再“活”而变得死死的了。大家都不说缘由,脸上却挂着深不可测的微笑。
她见他回屋时依然一脸迷惑就笑他木榆脑壳,就把樱桃小嘴嘟在他耳边悄悄地告诉了秘密:
“难道真的忘了?小张曾是三只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