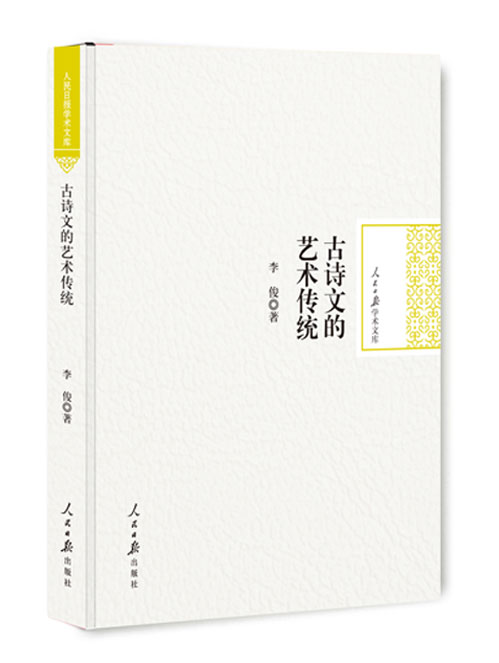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角度,分析了秦汉文学到唐代文学发展过程的艺术传统和思想传统,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优秀篇章分析、文体变迁研究、作家个案研究、题材发展研究、艺术思潮研究。作者并不追求对“古诗文的艺术传统”进行理论性的、总结性的、宏观性的回答,而是尝试多角度、多方位、长线索地切入汉唐文学,在具体研究中切开某种题材、文体的历史横断面,分析其艺术传统的内在变迁,在将问题进行具体化处理的过程中,有限度地展开理论思考。
作者简介
李俊 男,1976年生,陕西临潼人。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研究,出版过《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专著,并在《文学遗产》《国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多篇。
王道的可能性及其言说的逻辑——读《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论汉乐府诗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论先秦两汉文学中的思古传统——咏史与怀古主题溯源
贾谧与“二十四友”的是非
诗歌写作:一种文化的标记——论陆机五言诗写作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读江淹《别赋》
北朝后期诗歌创作心理的本土认同
庾信诗歌创作与《左传》
初盛唐之际七言律诗的嬗变
杜甫与七言律诗
七言律诗之难
杨巨源的诗歌创作
杨巨源生平事迹杂考
杨巨源诗集小考
《长恨歌》与李杨故事
王道的可能性及其言说的逻辑
——读《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一、王道和霸道的对话关系
《孟子·梁惠王》中有一篇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对话一开始,齐宣王劈头便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而闻乎”?要孟子回答。孟子听到齐宣王的提问之后,立即从儒家学者的角度直言否定了这一问题的意义,认为没有必要讨论它,而用“王道”的话题将其取而代之。于是后面的全部对话都围绕着“王道”展开,“齐桓晋文之事”的问题似乎被完全悬置起来了。
然而事情似乎又未必这样简单。所谓“齐桓晋文之事”,是指关于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和晋文公的历史。春秋五霸的说法历来存在分歧,一般认为是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这五人之中,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最早的一位霸主。晋文公先因晋国内乱而出逃于诸侯之间数十年,一旦归国,不几年就成就霸业,奠定了晋国强大的基础,文公之后百余年间,晋国一直保持着大国霸主的地位,与南方的楚国相抗衡。其余的三位霸主中,宋襄公实际上争霸未果,秦穆公仅称霸于西戎,在中原的影响力不足,楚庄王则因为是南方势力,不为中原诸侯所重视,自成一个系统。所以,齐宣王仅以“齐桓晋文之事”发问于孟子,而不及其余,由此也可以看出齐桓公、晋文公二人称霸的事迹对后世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齐宣王的问题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一历史掌故的始末,而是有意从历史陈迹中探询“霸道”之术。可以说,这个问题不仅是齐宣王关心的问题,也是战国时期列国统治者共同的问题。孟子当然明白齐宣王这一问题的深意,但他自许为孔子之门徒,标榜仲尼之学,只研究和倡导王道,对时人热衷的霸道理论很看不起。所以他说“仲尼之徒,无道齐桓晋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孟子的这个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说《春秋》中对齐桓晋文之事就有记载,仅《论语》中孔门师徒讨论齐桓晋文及管仲事迹的片段就有不少,孔子对管仲辅助桓公成就霸业的功绩是十分称赞的,怎能说仲尼门徒不传桓文之事呢?很明显,孟子的话是不能这么理解的,否则就犯了孟子本人警示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错误,而应该遵守孟子提倡的“以意逆志”的方法,了解说话人在这里想表达的真正意图。孟子说儒家“无传”桓文之事,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深致其意,说齐桓公晋文公的霸道之术与孔子之学相比,真是不值一提,故而历来的儒家学者,对此不曾措意。这大抵与孟子所云“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的话相一致。齐宣王提出的话题是霸道,孟子提出的问题是王道,王道与霸道是相对立的两种主张,这就决定了整篇对话中孟子向齐宣王鼓吹王道的全部内容,实际上与文章一开始齐宣王提出的“齐桓晋文之事”存在着潜在的“对话”关系,只是这种对话关系在本篇中仅处于隐而不显的状态而已。
《孟子》一书和《论语》一样,是以语录体和对话体为主的。所不同的是,《论语》简约而含蓄有味,委婉有致。《孟子》则加大了演绎的成分,故而篇幅较长,谈论辩难的情形较为周详,意尽句中。《论语》以孔子为主,但其他门人的言语风范和思想见解亦大有可观,与孔子的言论相互衬托照映,相得益彰。而《孟子》一书唯以孟子一人为本,其他诸人,皆言无可采,这样就全力突出了孟子个人的思想锋芒和影响力。相对来说,《孟子》中最为完备周详而又曲折尽情的篇章即《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和《滕文公上》“有为神农氏之言者许行章”。前者是游说齐宣王推行王道,后者是批判异端邪说,情形稍有不同,但都出于孟子宣明儒家思想的至诚之心。
孟子曾经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由周而来,七百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意思是说,自西周武王以来,至战国中期,已经有七百余年历史了,该有圣王明主现世治平天下了吧,如果真有明王降世,那么辅佐明王平治天下的人,除了我孟轲,还有谁呢?可见他自视甚高,而且在他看来,为了推行王道解民倒悬而游说诸侯,和世俗之人干进求利自不能同日而语。“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绝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诸沟中”。因此,孟子游说诸侯是以尧舜之道致君,而不是屈己求人,枉己正人。
在孟子的一生中,他曾先后游说过滕、宋、邹、鲁等小国,虽然他认为邦国不论大小强弱,皆可以施行仁政。但他还是受到战国时期流行的战略思想的影响,认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由梁、齐这样的大国来实现仁政,更加符合他的愿望。因此,邹、鲁、滕、宋的统治者主动邀请孟子,他才去这些小国宣教,而游说梁齐之主,则是孟子主动前往的。所以梁惠王初见孟子,便云:“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相对梁国来说,孟子对齐国的兴趣更大。在齐威王时代,他就曾到过齐国,而当时齐王任用田忌等名将,力征四方,声势浩大,对孟子宣扬的仁政王道不甚重视。所以威王只是出于礼贤下士的态度,馈赠孟子一百金,孟子没有接受,失望而去。当威王下世,宣王即位之时,梁惠王也下世了,襄王即位。可是在孟子看来,梁襄王“不似人君”,难有作为,于是他再次入齐,准备游说齐宣王。也许,孟子也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梁国已经不可为了,齐宣王能否接受他的思想,也就在此一举了。此举如果不能成功,那么他所期待的明王,他所期待的时与势,恐怕都不可再得了吧,因此孟子游说齐宣王就显得十分用力,再加上此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已经日臻完善,辩才也至老境,在《孟子》一书当中,与齐宣王交谈讨论的内容保留最多,分量最重,或许原因就在此中。而《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向宣王鼓吹王道,周详备至,沉着婉转,用心之重,用力之深,也与此不无关系。
二、王道仁政的两个基本问题
当孟子提出王道的话题以后,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其二是“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这两个问题是有关联性的,但层次不同。前者要求孟子明确阐述王道仁政的理论依据,是“王道仁政何以可能”的问题,后者要求孟子回答国君之所以愿意施行仁政的内在道德根据,是“为国者施行仁政何以可能”的问题。前者表明孟子王道思想的内在逻辑,后者表明孟子的“说辞”展开的内在逻辑。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说服齐宣王,而说服齐王才是他的目标。
孟子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第一个问题他化繁为简,扼要而言,一语中的。当齐宣王问“德何如则可以王”时,孟子的答案十分简单又异常明确,“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提出王道仁政的根本就是“保民”。应该说,在一般人看来,王道仁政应该有一套十分复杂的理论,很难用一言一语解释清楚。齐宣王的提问方式实际上就包含着对这一理论难题的顾虑,“德何如则可以王矣”。王者,王天下也,是天下至难至艰的事情,是天下最伟大的功业,而这样的功业仅靠一个“德”字来取得,仅从一个难以言明的“德”上建立,真让人难以理解。齐宣王就不能把“德”和“王”在认识上联系起来,才提出了“‘德’怎么可能‘王’天下呢”这样的问题。正因为一般人会觉得王道仁政是十分难解的,所以孟子才深思熟虑,拈出“保民”二字,用最简单的话明白回答,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疑惑一扫而清。用高度概括的两个字扼要而言,让听者一下子抓住王道仁政的思想要领,高深莫测的问题一下子显豁起来。由“德”而“王”再也不是一个理论难题,甚至也不再是一个实践难题。因为从理论上说,“保民”二字作为中介,将“德”与“王”联系起来了。有仁德则可以爱民,爱民则能保民,保民则天下归之。这其中的逻辑是非常顺畅且清晰的。在实践的层面,施行王道仁政也没有千头万绪般繁杂,只要抓住“保民”二字就可以了,简单易行。
由此看来,“保民而王”这句话真是举重若轻,看似平易,实则是孟子用心锤炼的关键命题。因为孟子懂得怎样用恰当的言词去抓住听者的思想,所谓“我知言”就蕴涵着这样的思想。当人们把王道仁政看作难懂、难行的思想主张时,要推行王道仁政,必须要将它简化,甚至口号化、标语化,让听者闻言知义,心生向往。通读这篇对话后,我们知道在孟子的思想中,施行仁政德政进而统一天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他要全面、详细地加以阐述,恐怕这也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但当遇到像齐宣王这样的人,既对王道缺乏兴趣,又把王道看作是迂阔难解的理论主张,孟子就不能急于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和盘托出,而只能有意先将其简化扼要地提出来,培养出听者的兴趣,不让他望而生畏。孟子的这一策略显然是奏效的。因为齐宣王听了他的回答后,随即就问:“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不仅兴趣极高,而且主动将其与自己的政治能力相联系,心为所动,大有跃跃欲试的意思。
应该说,齐宣王问“德如何则可以王”,孟子回答保民而王,这是整篇对话的核心思想。这篇对话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问一答展开的,是这一问一答的拓展和深化。我有时臆想,如果把这一篇对话放在《论语》中,如果这个对话是在孔子和他的门人,或鲁卫当政者之间发生的,那么,我们可能读到的就是下面一段内容了:
或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言简义丰,令人深思。《孟子》的文风不同于《论语》的地方,主要是孟子对自己的思想主旨有许多发挥,孔子的话则经常是引而不发。然而孟子之所以如此发挥以力求尽意,则又是不得已的。因为他有明确的主观愿望,这个愿望就是他要“说服”对方,他希望自己的言论可以打动对方,并将其引入到自己的思想逻辑中来。单纯表述自己的思想主张是容易的,而要因之以说服他人就难了。因为这就要求他不仅将自己的全部思想主张的内在关系梳理清楚,而且要从他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寻找到一条可以通往圣谛的道路,使对方不仅觉得儒家的主张言之有理,而且行之有方,切合对方的实际,合乎对方的愿望。
于是,孟子就不得不面对第二个问题:“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采用了化简为繁、原原本本、从头说起的办法,不如此,不足以找到“说服”对方的切入点。只有将第二个问题探讨到一定的程度,让宣王觉得自己有能力施行王道仁政,也愿意施行王道仁政,然后再与第一个问题会合,重申王道仁政的深刻内涵。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就构成了本篇的两条基本线索。一是阐明思想,二是说服对方。这两条线索是交错在一起的,因此,整个对话的话题开阖断续,不拘一方。时而说到堂下之牛,时而说到鸿雁舆薪,时而泰山北海,真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而贯注其中的一股暗流,则不外乎这两个问题。最终由情入理,将齐宣王引入王道至理之中。
……








